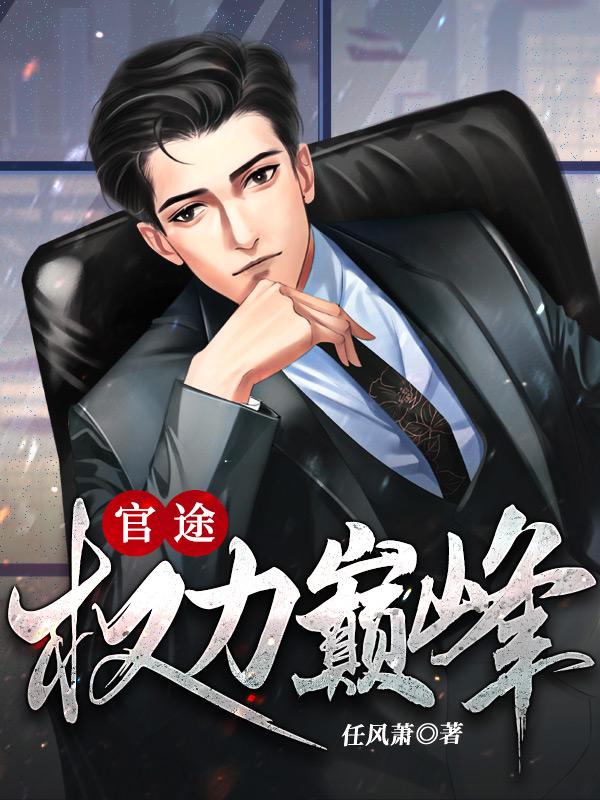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外翁病倒(第1页)
余静昭的眉头紧锁,脸色惨白,脚步匆匆如同心脏跳动的频率,每一步都显露出对谭阿翁现状的极度焦虑,她几乎是在与时间赛跑,急切地朝家的方向疾走。
情急之下,她发猛地推开家门,径直冲进了谭阿翁的卧房,她本想高声询问,可在她一见到谭阿翁躺在床上被郎中把脉扎针时,又即刻收住了步子。
房间中央,谭阿翁静卧于硬木床上,脸色苍白而略显疲惫,额头上隐隐可见细密的汗珠。
身侧的郎中手持一根细长的银针,照着古籍上的经络图,精准地找到了谭阿翁腕部的穴位。
他的手法稳定而熟练,轻轻刺入皮肤,缓缓推进,仿佛在引导着一股看不见的气流穿越脉络。
谭阿翁虽然年事已高,但面对针刺却显得异常坚忍,只是眉宇间偶尔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抽搐。
加之周围摆放着一些精致的药瓶和瓦罐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气,这股气味似乎也带给了他些许安慰。
不一会儿,郎中便给谭阿翁施好了针,待他将那些细长的银针从谭阿翁手臂取下,他就收拾起药箱来,转身对谭阿婆说:“阿翁不过是染了风寒,加之操劳过度,年纪大了,就有些虚了,平日里多吃点好的补补,今日我开些药方来,每日三副,皆饭后服用。”
于是,谭忠便领着郎中去大堂里写方子,留下一屋女子在身旁照料着谭阿翁。
施针后,谭阿翁的脸色确实好转了些许,但依然没能清醒过来。
余静昭也不知如何是好,她这几日全心都投在了谭记糕点铺的经营上,竟没留心谭阿翁的身体状况。
当初她决意要开铺子时,手头还缺了钱,可以说,她盘铺子的钱,除了少数零头,余下的大部分,都是靠着谭阿翁这么些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银两,二老本打算用这钱给自己打口棺木,却先将那钱袋给了余静昭。
谭家本就不够富裕,还得供着在镇上私塾听学的幺子谭义,加之家里又添了阿虎一张嘴,这回只有靠二老拮据才得以攒下这些家底,没承想他这一病,家里能干活的劳力又少了一个。
对啊!
谭家应当还有一人才对!
那不正是余静昭一直未能见到面的她二舅谭义吗?他爹都病倒了,他这做儿子的倒不至于还在镇上享受生活吧!
说办就办,余静昭等谭阿婆给谭阿翁喂完药后,轻手轻脚地将她拉到门外去,悄悄问道:“外婆,我想问一下,你可知我二舅住在何处?”
谭阿婆反倒警醒起来,反问道:“你问这个做甚?”
“我从未见过二舅,现下外翁病了,我觉着二舅应当时要知晓的。”
余静昭本以为谭阿婆会应允她的做法,却未料想,她竟一口回绝了,而她给出的理由却是“不愿打扰她温习功课”
。
余静昭不明白,何时科考之事要比爹娘性命更为要紧了?真是荒谬至极。
即使谭阿婆不愿告诉她谭义所在之所,她哪怕要自己一家一家搜寻,也誓要将他找出,亲自带到谭阿翁的床前。
正当她气势汹汹地迈出房门时,萧四的声音却在她耳畔响起:“父母之爱子,则为之计深远。”
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,余静昭发觉萧四方才竟一直倚门框上听着她和谭阿婆的谈话,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来。
“你在这儿说什么风凉话?”
余静昭皱起眉头来,显然面露难色。
可萧四却不紧不慢地同她一一道来:“你可知当下那些平民百姓前赴后继之路?”
“你是不是想说科举才是众望所归?”
余静昭也抱起手,同萧四攀谈起来,“大家都在走科举之路,反倒是鄙弃我走到这条行商之路,可对?”
萧四微微点了点头,继续说道:“既然你心知肚明,为何还要违背谭阿婆的心意?”
- 私吻蝴蝶骨璇枢星
- 替嫡姐爬上龙床,她宠冠后宫苏漫漫
- 归雾青炽
- 不乖(姐夫,出轨)夏多布里昂
- 七零大杂院小寡妇香酥栗
- 偏心我是认真的宜栩
- 无敌从觉醒武器大师开始乾上乾下
- 重生七零:糙汉老公掐腰宠一尾小锦鲤
- 他说我不配游湖喝着茶
- 官途,搭上女领导之后!平和心境
- 巅峰红颜:从咸鱼翻身开始老司机
- 不怪他!睡芒
- 我的年轻岳母番茄炒鸡蛋
- 潘多拉的复仇一颗仔姜
- 女神攻略手册慕歆尘
- 陈放顾静姝官道凶猛
- 以你为名的夏天任凭舟
- 蝶变麟潜
- 龙傲天的反派小师妹飞翼
- 骤落几京
- 直播写纯爱文的我在虫族封神MRA
- 结婚而已蒋牧童
- 他的暗卫女王不在家
- 男主怀了我的崽顾西子
- 官婿美人香刘志中张宏阳
- 云婳谢景行三尺神明
- 投喂流放罪臣后,她被迫现形了竹生焉
- 归雾青炽
- 重生表白失败,校花急了水果饺子
- 乖戾病(骨科高h)沉郁白
- 穿书后成了狼孩余书乔
- 官路浮沉争渡
- 巅峰红颜:从咸鱼翻身开始老司机
- 七零大杂院小寡妇香酥栗
- 见微知著(弟妹 H)乱佳音
- 杨凡吴雪兰徒儿下山了
- 诱奸儿媳旁观者
- 触手怪她只想生存星棘
- 千里宦途小豌豆本尊
- 乱花渐欲迷人眼(高h禁忌合集)风星子
- 官婿美人香全文完结开叫
- 官道征途:从跟老婆离婚开始蔡刀
- 官梯险情鹰飞草长
- 强者是怎样炼成的老肝妈
- 医道官途帷赫
- 赛博剑仙铁雨半麻
- 一品红人山间老寺
- 官途,搭上女领导之后!平和心境
- 龙凤猪旅行团珠玉在前
- 绝品宏图秦阳方媛
- 从一人开始成为诸天最强店主夏至夜深
- 我的弟子遍布全球胖瘦君
- UMA合集莹莹灿灿的高孝恭
- 冲喜弟妹诬告病娇大伯哥后带球跑红色的小麻袋
- 离婚后,美女总裁跪求复婚家有大魔王
- 我从修真界回来天庭的冷漠
- 万人迷萨摩耶,勇当恶毒女配!草莓奶冻七分冰
- 代号战神大漠孤羊
- 沅陵案空空如也
- 为名利分手,我成巨星你哭什么?三月的救赎
- 官路仕途:重生后一路狂飙煮茶化雨
- 温律师的隐婚小娇妻薄荷绿
- 我乃道主醉漾清风
- 把我推给闺蜜后,合约妻子哭惨了长寿仙
- 星海寻谜金晓玥
- 放开,为师不是这样的人!五行不缺土
- 这个大宋,女妖好多啊一眼万念
- 丹娘柔心糖
- 寒门帝师我是乌鸦
- 祖龙归来万界之主清杨子
- 割鹿记无罪
- 我用垃圾食品换仙丹,赢麻了锦鲤惊岁晚
- 重生之逃生舱叫我大雄
- 亘古路理非梦
- 无限但不恐怖违规的便利店
- 全球断电:重返冷兵器时代狂暴熊
- 百晓书馆,寻人遇上的麻烦事潇小乙
- 她叫阿凉阿栗子哎
- 星火迷局红胜
- 斗罗:开局一只汤姆猫封涯者
- 穿书之种田人被迫提剑整顿修仙界繁花一叶
- 美漫:从奥斯本开始成就科技之神焦糖蜜柚
- 同时穿越:正常人只有我自己?琴酒不喝雪莉
- 超兽武装之为何而战飞天战龙
- 机战:先驱者的归来五对轮
- 山上跟师父练武,下山带媳妇修仙吃烧烤没有酱
- 三胎三劫,霍少奶奶蜕变成王晓砚
- 日落之后现实与幻想的黄昏江呓琅
- 君临诺贝兰渡鸦与英灵殿
- 我父刘玄德网文老大爷